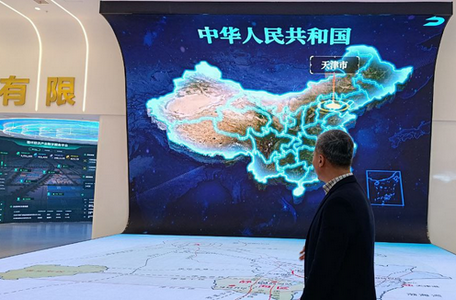最近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不仅为中亚国家,也为全世界勾勒出了新的前景。有人认为这甚至成为了改变现有世界秩序的宣言。这些假设并非偶然:峰会期间,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所谓的»全球治理倡议»,普京总统也对此表示支持。
专家们认为这一倡议体现了中国对世界政治观点的转变。HSE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研究综合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认为,中国新倡议的目标是逐步改革全球机构和国际行为准则,本质上是形成符合中国观念和利益的新国际秩序。
观察人士认为,上合组织正从宣言转向制度化和创建常设机构。其中包括将设在塔什干的»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通用中心»以及设在杜尚别的»上合组织禁毒中心»。
西方对习近平的新理念持谨慎态度。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试图用上海合作组织取代联合国。这种怀疑当然立即遭到中国人及其战略盟友(如俄罗斯)的反驳。然而,考虑到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印度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以中国为中心、与西方作对的世界理念似乎并不那么幻想。
这样的世界可能如何存在,现在就可以基于中国与中亚近年来形成的关系模式来理解。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中华帝国的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实践-至少从非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共产主义者的殖民主义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无疑是中亚主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由于苏联时期遗留的习惯,俄罗斯被视为宗主国,而该地区的共和国则类似于省份。尽管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已独立,但它们在政治、经济甚至日常生活中仍不断向莫斯科看齐。
甚至出现了荒谬的情况。比如,90年代在哈萨克斯坦,中国组装的计算机在商店里以过高的价格出售。原因是这些计算机由俄罗斯销售商从中国采购,运到莫斯科,然后由哈萨克商人购买并运输到哈萨克斯坦。这种做法代替了直接从中国进口到哈萨克斯坦。
苏联时期的遗产如此重要,以至于90年代末突然发现,年轻的哈萨克知识分子不懂母语,因为他们一生只说和读俄语。那时甚至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大公司高层管理中没有一个会说哈萨克语的人。年轻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中开始兴起学习哈萨克语的运动。
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继续在该地区实施其政治和经济计划。中国变得富裕,并逐渐加强对中亚的影响。最初,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基于相当简单的目标。2004年,中国专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李立凡和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丁世优如此表述:»经过长期探索和精心准备,北京的中亚战略已经确定。它旨在依托上合组织...实现其战略利益,这些利益主要集中在开发中亚资源方面。» (年鉴“世界和地区政治中的中国。历史与现代性。”第 XIII 期(特刊)。IKS RAS,2008 年。第 148 页)。
这些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新殖民主义的。总的来说,中国在20世纪,尽管有共产主义修辞,显然走上了殖民主义轨道。很难谴责它:中国人需要从20世纪灾难-帝制垮台、内战和日本占领-造成的深渊中爬出来。毛泽东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意识形态运动也没有给中国增加稳定性。邓小平的改革略有改善,但中国距离发达西方国家,甚至距离邓小平为经济设定的»小康社会»目标还很遥远。
当时该地区国家不仅积极出售自然资源和自然垄断资源,还向中国借款。这给了它们即时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威胁着包括丧失主权在内的严重麻烦。至少一些政治学家和民族社会政治运动代表是这样认为的。
总有人居高临下
尽管与中国合作有明显好处,但在中亚国家,首先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开始滋生恐华情绪。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有很多,从历史原因(如与准噶尔的战争,准噶尔背后站着中国人)到政治原因(中国在其领土上歧视一些少数民族,其中包括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
不过,恐华情绪最明显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在其公司开发的领土上的政策。在中亚建立企业时,中国人通常也带来中国工人,剥夺了当地居民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即使当地人在中国企业工作,也被视为二等人-至少他们是这样理解中国管理层对待他们的方式的。在他们眼中,情况是这样的:文化上陌生的中国人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并从他们的自然资源中获利。
哈萨克民众的不满在2016-2020年的反华抗议中得到体现。最强烈的抗议浪潮出现在2019年秋季,始于扎纳奥津市。当地居民反对与中国合建企业,并呼吁政府不要向中国而要向西方借款。反对中国扩张的集会当时在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举行。
中国人对当地居民的轻蔑和傲慢态度更是火上浇油,当地人自然不愿忍受这种态度。当然,苏联时期俄罗斯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不尽如人意,但那时官方推行的是在统一苏联民族框架内所有民族平等的政策。虽然有关于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楚科奇人等相当冒犯性的笑话,但人们都明白要在一个国家生活。在此背景下,不同民族代表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甚至友谊都是常事。当然,仇外心理也存在,但大多数情况下,它具有所谓的“横向”特征:我们不喜欢他们,因为我们害怕,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对他们有什么期望。但建立在苏联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影响。无论如何,仇外心理被遏制住了-苏联共产党的全视之眼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它。
与中国人的情况从一开始就不同。2000年代,他们来到中亚共和国的土地上如同主人一般,俯视当地居民。不过,这种做法不仅是普通中国工人和商人允许自己的。2016年,时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汉晖对阿斯塔纳加强对中国公民签证要求感到不满,直接爆发:»这太粗鲁了,这是羞辱!他们(哈萨克人)知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其他民族和国家代表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首要和主要原因是中国人习惯的等级制度,这渗透了他们的整个文化。传统上这里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关系中一方或一个人必然高于另一方。这也涉及家庭关系:例如,在汉语中,»兄弟»这个词几乎不单独使用,兄弟总是哥哥或弟弟,姐妹也是如此。甚至在中华帝国,祖父母之间也不平等:父系祖先被认为比母系祖先更重要、更有意义。
这种现象形成了数千年。最初,它显然与祖先崇拜有关,由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向祖先献祭。后来,这种秩序被儒家哲学巩固,儒家提出了»孝»的概念-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以及晚辈对长辈的服从。这个体系通常包括家庭关系、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以及臣民对君主的忠诚,君主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定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父母»。
汉族与穆斯林
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带着项目和资金来到中亚时,处于管理层地位,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首先是当地居民,则处于下属地位。下属自然有义务听从管理层并仰视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孝»的特点是,作为服从和恭敬的交换,上级为下级提供庇护和保护。然而,这个规则显然不完全适用于中亚居民-同样由于中国世界观的特殊性。
根据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大地呈方形,上方是圆形的天空。天空覆盖的区域叫做»天下»。在其中心生活着智慧、高度文明的中国人。在边缘,略微被天空覆盖或完全不被覆盖的地方,生活着不同程度野蛮的蛮族。
尽管这种观念古老,但中国人将自己的祖国视为宇宙中心的观点至今仍然存在。野蛮民族并不总是值得文明对待,是否给予他们庇护和保护,这由中国人自己决定。毕竟,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资源和服务获得了金钱,还要什么呢?
情况还因中亚民族历史上信仰伊斯兰教而复杂化。中国人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长期以来非常复杂。一方面,中国境内长期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通常用»回»字表示。另一方面,普通中国人传统上对穆斯林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拒绝食用猪肉(中国的主要肉类)、饮酒,以及对描绘人和动物形象的绘画持否定态度,这在《古兰经》中是被禁止的。此外,早在中世纪,穆斯林在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就非常成功,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嫉妒,导致了许多相互误解。
实际上,寻找汉族对回族穆斯林相互反感的原因并不困难。据传说,同治帝(1861-1875年)曾说过,汉族鄙视回族仅仅因为他们是回族。这让穆斯林人感到受伤和冒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挑衅汉族人发生冲突甚至打斗。同时,统治的满族王朝还故意挑拨汉族和回族,使他们在相互冲突中削弱,不将愤怒转向帝制政权。
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对回族的怀疑态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移到了中亚民族身上。无论如何,中国人与当地居民关系中经常出现傲慢和轻蔑的态度。
不过,中亚在这方面并不独特。中国人以类似方式,即作为野蛮人,对待几乎所有外国人。可以理解,这种立场不是由有教育的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他们明白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独特性,因此没有理由轻蔑地对待他们。然而,中国不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普通民众喜欢展示中国对外国野蛮人的优越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展示可能是真诚的:中国普通民众相信真正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只有他们才有。如果你与中国人建立稍微密切的关系,他必然会声称你需要学习文化。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你野蛮的外国文化,而是真正的,即中国文化。
应该相信软实力吗?
在与中华帝国接壤的国家公民所担心的恐惧中,包括对经济被渐进占领的担心和失去领土的恐惧。不能说这完全没有根据。
苏联解体后,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出现了边界问题。这些问题在哈萨克斯坦案例中特别明显,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最长-1740公里。然而,到1999年,经过密集谈判,中哈边界划界过程完成。根据协议,407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划归中国,537平方公里留在哈萨克斯坦。
中吉边界也在1999年最终划定。根据两项协议条件,吉尔吉斯斯坦向中国转让了约5000公顷争议土地。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情况最为复杂。中国对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境内三个争议地段提出领土要求,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据不同资料,中国获得了1000到1500平方公里。目前,中国还没有坚持立即无条件执行其要求:塔吉克斯坦已有将争议领土作为偿还对华债务经验。
然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领土要求还有更古老的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曾经中国以东的巨大领土被蒙古人占领。但当时的蒙古可汗不仅仅是蒙古人,他们还是中国元朝的皇帝:从忽必烈汗到妥懽帖睦尔(顺帝)。因此,几个世纪前,现今中亚的领土属于中蒙帝国。现在的中国普通民众完全知道这一点,并时常在私人谈话或主题论坛上不失时机地提醒这一点。当然,中国领导层官方上不支持这种谈话。
然而,土地不一定要夺取-可以租借甚至购买。就在不久前,中国几乎出现了这样的机会。
哈萨克斯坦人很好地记得2016年全国如何爆发大规模抗议,反对《土地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允许长期租赁和出售农业用地-包括向外国人。哈萨克人当时害怕大片领土可能转入中国人控制。当局最终没有敢明显违背民意,宣布暂停修正案生效,后来完全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土地。
尽管如此,中国并未减弱压力,使用所谓的软实力-这个表达随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而广为流传。也许正是这种软实力最让中亚民众担心。这并非没有根据。软实力的作用不易察觉,它秘密地达到目的。既然如此,是否应该相信软实力,如果甚至无法理解它何时变成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软实力并不比粗暴力量好,甚至可能更危险。
中国人如何在中亚使用软实力,以及他们在新条件下如何对世界其他地区使用软实力?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单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