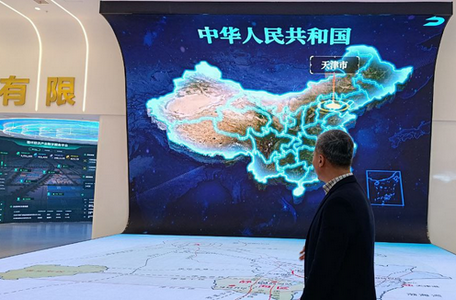要想了解乌兹别克斯坦某个地区大多数人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就得去集市。它会直观地展示一切,许多东西无需言语便能说明。在2025年9月与安佐尔·布哈尔斯基(Anzor Bukharsky)一起完成了费尔干纳盆地小城镇的摄影之旅后,我对此深信不疑。
安佐尔·布哈尔斯基是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民族志、风俗和街头摄影大师班的组织者。在联合考察了高山小镇格兰之后,他邀请我作为向导,带领一次前往费尔干纳盆地的快速摄影之旅。同行的还有俄罗斯风俗摄影师奥列格·格沃尔科夫(莫斯科)和鲁斯兰娜·科尔米利奇科娃(新西伯利亚)。
我们在旅游旺季开始前进行了这次创作考察。夏日的炎热尚未消退,丰收才刚刚开始,婚礼和其他庆典都已推迟。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工作日,头顶无情烈日。日常生活的图景。不追求新闻性、记者报道、社会或哲学概括。用相机记录的旅行笔记。近距离但非选择性地观察随机路人的面孔。
同时,作为乌兹别克斯坦汽车旅行的爱好者和积极参与者,我们决定体验一下塔什干的汽车共享服务。我们共同的朋友帖木儿·努马诺夫,曾在过去的联合考察中担任娴熟的司机,这次正好没空。我们不想雇出租车,并非出于费用考虑。
塔什干的出租车司机有五种类型:DJ、政治学家、宗教布道者、前经济部副部长以及讲解«规矩»的江湖大佬。恕我直言,他们中没有一位适合作为我们此次旅行的有效伙伴。
安佐尔决定自己开车,从塔什干的一家租赁公司租了一辆UzAutoMotors 生产的相对较新的Chevrolet Cobalt汽油车,每日租金45万苏姆(合36美元)。外加200万苏姆(合160美元)的押金。这是为了应对我们的车被路边雷达记录到交通违章的情况。
周一中午左右,我们艰难地驶出首都的拥堵路段,上了塔什干-安集延-奥什-喀什的国际高速公路A-373。然后我们以«一人驾驶,三人七嘴八舌出主意»的模式前进。几乎没注意到就穿过了海拔2268米的坎奇克山口。不过,在这个季节,它并没有什么视觉吸引力。初秋时节,乌兹别克斯坦的自然色彩都被晒得发白,甚至连山景也沉闷乏味。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驶下山口,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有些地方每平方公里居住着超过800人。密度比印度还大。但在完全沉浸于这片人海之前,我建议同事们先去一个原始角落看看,那里保留着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前这些地方的模样。
疗愈沙丘
过桥跨过锡尔河后,我们转向西南,行驶了大约十五分钟,在快到布斯顿-布瓦镇的地方,遇到了一个特别的«海滩»。在耕地的环绕中,是两座完全野生、荒芜的沙丘,沙粒呈灰白色,长着梭梭树、柽柳丛和沙拐枣。关于费尔干纳州遍布的这种遗迹沙丘的起源,我已向Fergana的读者详细介绍过。简而言之,它们是阿克库姆沙漠的残留,这片沙漠从远古时代直到20世纪中叶一直占据着费尔干纳盆地的中心地带,后来因灌溉植棉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人口爆炸而退缩。
布瓦伊丁区的这个沙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里至今仍保留着一种中世纪习俗。在八月末九月初,阳光依旧灼人但已不至致命时,成群结队的人会聚集于此,待上一整天,进行热沙浴-希望能治愈皮肤、骨关节及其他一些疾病。从每年不仅周边村庄,甚至乌兹别克斯坦其他相当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前来接受治疗来看,这种疗法对有些人确实有效。或者他们认为是有效的。人们将手脚,有时甚至是整个躯干埋入沙中,只露出头和胸部-以免引发心脏病。他们用自制的遮阳篷来防止中暑。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种疗法具有风险性。不仅短期,长期后果亦然。然而,布瓦伊丁区官方以其长寿老人而闻名。例如,居住在此的胡瓦伊多·乌马罗夫(女),在2025年官方年龄已达130岁。据官方统计,有四位当地居民年龄超过百岁,另有数百人年龄超过80岁。不过,没有数据表明他们是否曾接受过沙浴。
费尔干纳的地方志学者认为,关于沙丘疗效的传说与12世纪中世纪神秘主义者霍加·巴亚齐德的崇拜有关,他的陵墓就在附近。他是传奇苏菲派导师艾哈迈德·亚萨维的侄子。布瓦伊丁区共有十处与著名苏菲派导师的名字和活动相关的圣地。
«沙浴后五天不能洗澡。七天不能喝冷饮和酒精饮料,»一位当地治疗师向俄罗斯客人们解释道,这彻底打消了他们哪怕部分体验此疗法的念头。况且太阳也已西斜。利用«黄金时刻»的所有视觉优势,摄影师们与其他访客一起离开了沙丘。
我们在浩罕一家偶然遇到的青年旅社过了夜。旅社价格不贵,也相当不错,只是不含早餐。向这座古城、浩罕汗国首都的美景致敬的计划,被两个实际困难打乱了。首先,交通极其繁忙且混乱。安佐尔白天开车已经累了,晚上坚决拒绝再在这种交通状况下挣扎。步行也不舒适-受管控的人行横道太少,人行道非常狭窄,而且还停满了汽车。
早上八点,我们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集市上吃早餐,暗自得出结论:浩罕可能不会成为我们摄影探索的主要基地。
«你说过费尔干纳盆地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但我还没感觉到,»奥列格·格沃尔科夫调侃我。我没有争辩,果断地将路线设定前往马尔吉兰。
集市之集
费尔干纳盆地的高人口密度其实很明显,从浩罕到马尔吉兰的公路几乎没有任何路段不属于某个居民点。一个村镇结束,另一个立刻开始。整整76公里的路程都是如此。安佐尔不得不一直以城市交通的速度行驶,多次用强烈的字眼评论这一特点。但他从未违反交通规则。
为了避免以70公里时速单调行驶的疲劳,我们在路边做了最多次数的停车和休息。例如,我们在公路不太繁忙的路段停下,当地村民正在晾晒第一批收获的作物-采摘下来的玉米穗或红色尖椒卡兰皮尔。我个人没能拍出高度艺术性的照片,但这一有趣的生活特色总算被记录了下来。
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到达了马尔吉兰-费尔干纳盆地最古老、最大的城市之一。摄影师们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过去,甚至更早世纪亚洲城市的建筑和生活风情,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生活的动态。
马尔吉兰向来被定位为伟大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的丝绸制造中心之一。至今这里仍大规模生产阿特拉斯绸和阿德拉斯绸-具有独特、可识别图案的纯丝及半丝织物。其古老的生产工艺于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毕竟,这里大多数人并不从事生产。城市经济主要集中在大型的服装集市和食品市场。私营部门非常发达。市民主要从事买卖和手工业,许多人在政府机构工作,维基百科这样描述马尔吉兰。
在马尔吉兰的第一站,我们停在了一条专卖门窗的街道,既有现代的塑料型材门窗,也有旧的、用过的,可能来自已拆除建筑的门窗。那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愉快地和当地小学生一起吃了冰淇淋。同时注意到当地生活中一个显著特点:两轮交通工具在马尔吉兰的街道交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不是摩托车,主要是自行车,以及轻便摩托车、摩托踏板车和小型摩托车。可能的解释是费尔干纳盆地中心部分绝对平坦的地形,使得两轮交通工具成为方便出行和货运的工具。在当地集市及周围狭窄街道的拥挤人群中,自行车和小摩托车灵巧地穿梭,如同激流中的小鱼。
中午时分,我们被热情地、几乎是拉着胳膊邀请去参观一个生产各种瓷砖的私人作坊。我愉快地利用了这个工厂粗犷的内部环境进行摆拍构图,这在我看来仿佛是某种时间与地点的原型。或者是我自己在这个太阳炙烤、秋天不按日历降临的地方的生活缩影。
«并非所有东西都让我感兴趣,但人们的开放和友善令我震惊。我肯定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也不确定将来是否会见到,»奥列格·格沃尔科夫承认道。
然后我们去了巨大的«科姆比纳特斯基»集市。这里出售当地丝绸作坊生产的布料。但不止这些。地毯、服装、床上用品、食品和家居用品-所有一切都杂乱地混合成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调色板。
安佐尔·布哈尔斯基愉快地在集市上度过了下午剩下的时光。但并未完全满足。
«这还不是那个集市,»晚上他对我说。«有一个超级集市,集市之集»。
我回答说我听说过。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租来的雪佛兰停在停车场,坐上出租车前往马尔吉兰郊区库姆特帕镇(当地地名如此),去往库什捷皮斯基集市。更准确地说,是那里的集市集群。其中包括:家具集市、木制品及木材集市、«法伊兹»服装集市、餐具集市、自行车及自行车零件集市、大锅集市、土坯砖集市、农产品集市等等,等等…
存在之底
我必须承认,在费尔干纳盆地我感觉不如在塔什干舒适。顺便说一句,在塔什干我甚至因个人生活需要也从不逛集市。更喜欢在24小时营业的大型超市采购一切。和所有首都居民一样,拍照我也更偏爱塔什干州西天山人口稀少、田园诗般山坡上那些忧郁的景色。马尔吉兰附近平坦如桌的表面上的人海,用不习惯的情感和感觉浪潮淹没了我。正如常言道,我走出了舒适区。同时注意到,我已经拍了这么多素材,连十分之一都无法向读者展示。
不知不觉中,我脱离了同事们,把相机放进包里,干脆坐在了一家茶馆里,合理地期待着安佐尔·布哈尔斯基和他的同伴们迟早-更可能是在下午-会被烤羊肉串的香味吸引过来。我享受着人群中的孤独,想象自己仿佛处于存在之底。在距离公认的现代文明中心数千公里之外。但同时又在宇宙的核心。这像是一种顿悟。也是我们旅程的一个转折点。
费尔干纳盆地摄影行中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时刻。第二天,在奥尔蒂阿里克区的贝拉雷克镇,我们参观了围绕并位于一座农舍内的广阔私人葡萄园。返回布瓦伊丁区后,我们与棉田里的采棉工进行了交流。
进入纳曼干州后,我们在古鲁姆萨赖镇拍摄了摆渡人和锡尔河上的自航渡轮,该渡轮在秋季因河水水位低而停运。
然后我们去了楚斯特市,逛了传统的楚斯特刀集市。安佐尔在那里找到了炉火正旺的锻铁作坊。
在三星级的S-Namangan酒店过夜后,我们一早用了四个小时就赶回了塔什干,在那里又堵了将近一个小时。总算勉强准时把汽车了租赁公司,没有因交通违章被罚一分钱。
我们短暂的远行远未穷尽费尔干纳盆地向摄影师们展示的视觉可能性,尤其是在不同的季节。但我们有意为未来的考察留下了几十个值得注意的地点、大大小小有趣的城市。以便有理由再次前往。